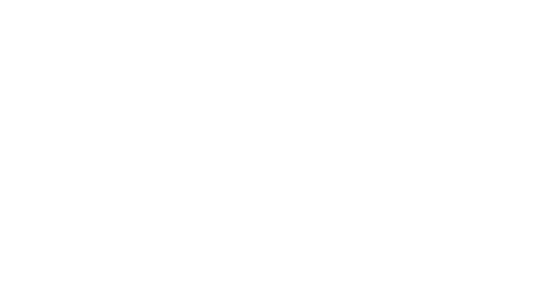文/楊禮安(台灣大學外文、社會系・OURs都市改革組織實習生)
儘管面對困難,OUR仍致力於推動居住有關的政策與法案,但他們也認知到這些做法是有侷限的,一些其他的策略也必須要被開拓。
垃圾飄盪在化糞池的汙水上,散發著臭酸味,一路從地下室淹到了一樓。褪色的殘垣斷壁,瀰漫著一片陰沉死寂。發霉的牆壁、生鏽的鐵窗、裸露的鋼筋電纜,以及腐爛的木工,散布在被遺忘的角落,毫無半點生息。獨居長者、藥頭、屍體與老鼠,窩聚一起默哀著城市的冷漠。夜裡,他們或許會悄悄離去,或仍困於此地。
這是三重29街曾經的一景,多年前被媒體報導,稱之為獨居長者的「失樂園」。在建商破產,強佔戶當起二房東後,這裡被市民長期遺忘,政府則礙於私人產權不清,遲遲無法有效的整治。如此駭人的地方,在都市留下了無法揮去的烙印,即使前陣子終於在媒體的壓力、政府的強推之下翻新。但這為何會在台灣發生?是甚麼讓這些住戶淪落於此?很多人批評,但很少人試著去回答。
我想試著去找尋答案。2021年春天,我將腳踏車停在OURs都市改革組織坐落於大我新村的辦公室。OURs(Organization of Urban Re-s,Rs 指的是 Re-design、Re-plan、Re-build 、Review、Revolution 等價值)是一個長期關注居住正義的非政府、非營利組織,三十年前緣起於許多人記得的無殼蝸牛運動。大我新村則藏身於熱鬧的信義區的南邊角落,曾經眷村歷史已經轉型成熱情的NGO社區,在其中也有疫情中幫助飽受飢餓弱勢戶的食物銀行,而建築本身散發著一股在冷漠的都市叢林中難尋的溫暖。
我跟組織秘書長彭揚凱聊了一下我的疑惑,他立刻點出了問題所在,但他眼裡流露一股更深層的憂心。「低薪高房價,老舊缺乏更新的住宅,管理的問題都只是居住議題的一些部份。若要簡單來說,就是台灣人沒有太多可負擔的居住選擇。」他不只關心無家者、獨居長者的居住狀況,更認為這反映所有人的問題,像是通常被認為有大好前景的青年,首先就迷失在高價低品質的租屋市場裡,因為在台灣根本很難找到好的房子。他解釋說台灣大部分都是重視經濟價值的建商在供給方,而消費者則只能依賴他們,額度不足的社會住宅以及租金補貼,則止不了近火。
不過儘管面對歷經困難,OUR仍致力於推動居住有關的政策與法案修法,但他們也認知到這些做法是有侷限的,一些其他的策略也必須要被開拓。我問彭秘書長那像29街的例子有什麼樣的解決方式。他反而提出一個叫「合作住宅」的概念,是一種自造、自我組織的居住型式,而不是建商或國家建造的。秘書長解釋,在歐陸越來越多社會問題是透過合作住宅的方式解決,像是貧窮、移民、高齡社會等問題。「類似的模式裡面,合作住宅也用在處理、回應街友的議題上,如何從街友從街頭回歸到主流社會裡。那他們有些方案是通過這樣的居住過程中,有比較好的過度階段讓他們達到最後的目標。」若是29街能重新由一個共同意向的社群培力,整合資源,並融入原本的弱勢戶,那甚至能連動當地的經濟與社會活力。但彭秘書長一邊解釋,也一邊看出了我的困惑。這些住宅究竟帶來了什麼樣的效應?它又能如何在台灣實現呢?
一個合作的住宅
在回程的捷運上,我抱著一本OURs翻譯的《合作住宅指南》,突然一位女士拍了我的肩膀,跟我解釋她對書中的內容很有興趣,問我知不知道玖樓,一個在台灣推動共居公寓的社會企業。「共居」曾幾何時已經變成了廣為人知的概念,自然而然的談合作住宅時共居的景象也隨即出現。但彭秘書長跟我解釋說,雖然合作住宅也是共居的一種,但我們現在談的很多共居,其實還是由建商或私人企業籌畫的,而合作住宅是更強調居民自組社群,參與生產的過程,可以說是在共居光譜中更激進的一端。那位女士後來跟我聊了許久,還錯過了該下車的車站。
書中分享了非常多不同的合作住宅案例,但他們都是由一群有共同意向與需求的人組成,進而參與公共空間的規劃與管理模式。政府、公民團體或建築專業者可能會輔助建造的過程,但合作住宅的核心概念還是一種由下而上的生產方式,強調住戶主動參與生活環境的規劃、實踐與維持。居民們在相互溝通、妥協、合作中建立的互信及默契,打造理想的居住環境,此過程更是之後友善共居的關鍵。
當孤獨已成21世紀的常態,合作住宅展現了社群連帶激發的效應,降低了現代都市人彼此疏離的感受。來自不同背景的人在一個屋簷下相互合作,合作住宅將人們的生活連結在一起,並且打造了能夠維持社會支持的公共空間。居民可以藉此機會精進組織與溝通的技巧,而許多人也在過程中展現自己的專業。公共參與與社區發展結合了不同的社會議題,像是社區裡提供性別友善的空間或給小孩與長者的照護中心。
[ro*sa]22就是一個在維也納的專為女性設計的合作住宅。一位建築師首先有了設計女性建築的想法,而隨即受到單身女性們的廣大迴響。雖然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女性,但男性家庭成員也不會被排斥在外,更有嬰兒於住宅中出生,小孩也能在花園裡奔跑。圖書館內更特別藏有女性主義相關的書籍提供居民翻閱,並定期舉辦討論女性權益與社會地位的工作坊。「跟別人一起住,讓我知道每個女性的需求其實也各有不同,應該予以尊重。」《合作住宅指南》書中提及一位現居其中的住戶分享。
合作住宅的經濟性更直接幫助受困於貧窮的住戶。因為建商、投資客無法從房子本身抽取利益,而如果方案規劃的好,則大部分的人都可以以可負擔租金入住。相比台灣昂貴又虛設的公設,居民自己規劃的空間也較能符合他們的需求。居民更可能透過共享家具、設備、廚房等等來降低一個人生活的開銷。考量到許多都市人沒有時間互動與煮飯,許多合作住宅計畫都推行共餐時間,可能是每天或每周,居民聚在一起分享食物、聊天。楚德之林(Trudeslund)就是一個1970年在丹麥成立的例子,它要求居民參與社區的任務小組,去分擔像是裝修、照顧小孩、煮飯等任務。因為這裡的居民重視社群價值,他們自願提供服務與舉辦活動,並相對的受到共同回饋。一位社區的青年分享他的經驗:「我特別喜歡一起吃晚餐還有一起決定事情―這是某種民主的實踐,所有的利弊都放在檯面上討論。」
開始打造社區
但我們如何實踐這樣的理念呢?從何做起?「合作住宅的概念就是人跟房子,那到底是先有人還是先有房子呢?這是很常有的爭辯。我們的看法是先有人,因為沒有人就沒辦法徵求資源。最剛開始找到志同道合的夥伴,過程中當社群、論述凝結夠清楚,我相信去爭取資源就會比較順暢。」OURs研究員詹竣傑,是一位在OURs負責合作住宅研究與推廣的工作夥伴,在接受我的訪問時提到。從國外例子學習到的經驗往往先強調社群組織的重要性。彭秘書長則說歐洲國家現在有一些招募潛在參與者的平台,平台本身則依照個人與共同的興趣有篩選的過程。甚至有些有成熟的政策支持,結合專業的諮詢,像是土地、建築、財務、會計、法律等問題。但他也提到:「就算我們湊成了一群人,我們要開始從買地、找建築師的方式,又會遭遇到非常多的挑戰。」
至於合作住宅產權型式是很多元的,土地建物本身有可能是向公家單位或民間組織承租的,買來則又可以是個人私有或共有於居民組成的合作社,通常共有的型式比較容易維持運作,但達成共識的成本也相對高。例如,卡爾斯霍斯特計畫(Karlshorst)就是一個公有閒置土地轉為社區意象性的住宅。柏林的一個非營利組織將這個舊校再利用為一個包容性的多戶住宅,包含長者、身心障礙者以及其他弱勢戶。然而,在缺乏政策的支持下,要在台灣找一塊類似卡爾斯霍斯特的地方實在困難。雖然台灣常見的設定地上權的方式能將公有土地長期租給私人單位,但多是商業使用,像是熟悉的京站、晶華酒店這種BOT案,政府很少用來幫助社會計畫。
「傳統上地上權的概念是基於怎麼樣可以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簡單講是價高者得,誰給的錢最多。」彭秘書長提到歐洲的常見模式是類似地上權的作法,但採定價的方式,以社會方案的內容評比作為決選依據。非常多的合作住宅透過這樣的方式拿到土地,他們比的是「社會包容性」,像是提供多少比例是可負擔,交流空間,或者是方案中促進鄰里融合的方案。「只是這種方式放在台灣脈絡就很難說服政府,他們覺得這樣是在圖利。」彭秘書長無奈地說。其他問題還包含財務以及政策的支持,但彭秘書長說在習慣跟建商應對的模式下,如果民間沒有對口作為擔保,那政府跟銀行無法想像他們的融資對象以及支持理由。「他們就覺得,那你就去做啊。政府很難意識到這樣的事情怎麼放到政策裏去思考,把它當作很一般的市場行為。」
OURs正在努力招募有興趣組織合作住宅的社群,一起嘗試突破以上的困難。像是台中的友善住宅合作社已經集結了一群希望一起養老的人們。他們在網絡上建立了一個社群,也舉辦過不少場工作坊,但仍未找到適合他們的土地。OURs跟其他組織仍不斷嘗試要推出第一個功的案例,以向台灣民眾證明這樣的作法是可行,且值得一試的。
OURs與合作住宅的相逢
為何在推動合作住宅的過程中面對如此多難題,而OURs仍願意帶民眾勇往直前?三十年前,一群空間設計的專業者有感都市議題缺乏討論,開始推了許多參與式規劃、社區營造、文化資產保存等概念。像是今日我們假日能去的寶藏巖聚落,在當初的規劃過程中也有他們的身影。然而,這些努力並不足以解決都市議題裡最嚴重的居住問題,彭秘書長表示:「這個城市百分之九十五的建築物都是住宅,但住宅雖然是最重要的議題,反而長期被忽略。」意識到此,組織從2010年回到無殼蝸牛運動的初衷,開始參與大大小小有關居住正義的政策改革。但是,揚凱與組織夥伴也感到台灣的居住結構改革是一條漫長且艱難的道路,而他們應該要提供民眾新的選擇。
彭秘書長說明了OURs這些年主要的任務:「對於台灣的居住問題上,我們過去的策略選擇只有兩類嘛。第一類我們希望透過住宅市場的改革,像是實價登錄、房地合一稅,甚至我們這幾年在談奢侈稅或囤房稅;另外一個除了市場之外,我們強調國家應該扮演更積極的住宅的補貼,乃至住宅提供的角色。但大概我們自己的一些反省大概是這樣,市場改革相對的速度效果有一定的侷限,國家量能有限的狀況下,我們思考要不要來想想,在市場國家之外有沒有一些其他的可能性,這大概是我們開始去思考提倡合作住宅這樣的主要原因。」對於撼動結構感到些許無力,引介合作住宅是OURs願意嘗試的新路線。「但不代表我們不該繼續市場改革,或監督政府進行社宅或補貼,只是我們認為應該提供台灣社會有一個多的選項。」
竣傑在另一方面則擔心組織長期談艱澀的議題不太好接地氣,即便他們一直嘗試跟一般大眾討論。他說合作住宅或許能夠稍微轉變他們只是一群專業工作者與研究員的形象。「我們常常辦演講,每個月都辦演講。可是這個模式到現在,應該要嘗試另一種組織議題的方式。如果要接觸一般民眾,要找一個實際上他可以來參與的。」他舉主婦聯盟成功的例子,主婦聯盟起初是以環境教育的推廣開始的,但發現談有機共同購買有很多人響應。「組織希望擴大影響力,但推動過程中,如果我們具體可以實際提供給你住的服務,更可以擴大在一般人中的影響力。」
參考其他在台灣有影響力的非政府組織,OURs思索未來有更多與民眾的互動,而他們希望能從提供住宅給有興趣搬進來住的人開始,但這一路上仍有跌跌撞撞。
台灣的合作住宅前景
在所有的倡議過程中,總是會有一些質疑的聲音出現,合作住宅在台灣也不例外。竣傑解釋說大部分的聽眾除了不了解概念之外,也比較在乎可行性,因為沒有一本教科書能清楚的給一套SOP。
而就算在歐洲國家,類似的選擇也可能只是少數,頂多在所有的住宅裡占比百分之三到五,雖然目前的趨勢是不斷在成長。「合作住宅在可見的未來裡面,他的確不會變居住的主要選項。但他的出現不只是他提供了有需求的人這種居住模式,事實上透過這樣的模式裡面,激發很多我們對居住問題的討論、想像。」彭秘書長提到很多社會實驗是借助合作住宅的方式進行的,像是近年來歐洲移民議題。在布魯塞爾,房價在十年之內翻倍,而一間名叫希望之家(L’Espoir)的合作住宅,透過社區土地信託,打造了移民在房價沙漠裡的綠洲。彭秘書長補充:「你當然可以講說,那這樣的案例到底可以提供多少難民居住?有但的確是有限,可是我覺得他們這樣的模式裡面,引發很多迴響與討論,事實上最後也慢慢反饋到政府的住宅政策。」竣傑同意合作住宅的用意是要與社會對話。他在年輕時候參與各種公共議題,知道改變很難,但他認為「具體的議題、有效的討論」仍然很重要。
有一派的批評是合作住宅會不會變成中產階級的享樂園,揚凱則果斷的拒絕這種唱衰的說法。他說與台灣主流的門禁公寓相比,幾乎所有的合作住宅計畫都願意對社會開放空間。「現在哪個住宅不是中產階級的取向?」他認為都市裡長出的相對開放的居住模式,追求更高價值,就不應該予以否定。「如果我們做出一個比現在好的住宅,例如好的規劃設計,那我自己覺得其實就是一個進步。」竣傑說。他認同合作住宅應該不只有可負擔或開放性的價值,像是參與生產過程本身就很難得了。但他也強調合作住宅與社會的互惠性:「如果跟政府爭取資源,我們覺得他要開放。」
當台灣正邁向與歐美國家社會人口轉型相似的道路時,合作住宅似乎也是一個回應多元新需求的方式。台灣逐漸受到高齡少子化的衝擊,同時多元家庭更帶來不同的社群想像。「我覺得在台灣比較需要談一些銀髮共老的合作居住的模式,因為的確非常多戰後嬰兒潮的世代,他們可能即將面臨往後20年的退休人生。」揚凱說組織過去很普遍的介紹合作住宅的概念,現在可以開始挑選特定的案例跟有特定需求的目標受眾談起。竣傑提到目前組織起來的人多半是有房子的人,他們自然會想要住的更好,那可是合作住宅另一方面訴諸的是沒有房子的人,這群人是OURs要積極去組織的。
「我跟幾個社會住宅青創戶聊過,幾個都蠻有興趣的。」他說。然而,OURs仍有非常多的任務需要突破。「我們缺乏是一個檯面先鋒性的計畫,如果有可以拿來推廣會更有真實感。」彭秘書長嘆了口氣,用袖口擦了擦拿下來的眼鏡。「例如我每次都講國外,但總是會覺得,放在台灣有一道非常難跨越的鴻溝。」也許在台灣令人擔憂的居住未來,仍需要一群踏實的理想主義者默默努力。OURs相信民眾的期待有朝一日能更加堅定,一旦台灣有真實的案例去證明說―阿他錢怎麼找到,地怎麼找到,他怎麼跟住戶溝通,怎麼被帶出來。
「所以我們除了介紹國外案例之外,我們也開始把台灣比較少數的案例,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彭秘書長在訪談的最後,這樣向我承諾。